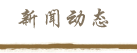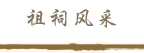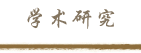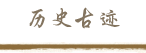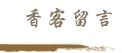人气排行榜
直面现实 尊重史实
2017-01-05 责任编辑:贤良港 我来说两句
|
直面现实尊重史实
——《读出历史的真相》答辩
文/许更生
2016年5月,《妈祖故里》特辑刊发了编者刘、朱二位合作的《读出历史的真相》。这篇《湄洲是妈祖诞生地文献史料汇编·前言》,其中事实之颠倒,语言之粗鄙,实属罕见,应予逐一驳斥。
一、海丝城市申遗,是谁在“打横炮”?
编者刘、朱二位提出,在海丝城市“申遗”的节骨眼上,有人故意“打横炮”,是误导干群、破坏大局。
事实又是如何呢?
报载,4月11日,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一行10人,对初步入选妈祖文化与海上丝路遗迹遗址名录的贤良港宋代古码头和贤良港天后祖祠等考察、调研。副市长张丽冰、市文广局局长刘晶洁、北岸开发区领导陈玉鹏、王义勇、陈远等陪同。6月6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带领专家来到莆田,进一步对湄洲妈祖祖庙、贤良港天后祖祠两处遗产点内的祖庙建筑群、宋代古航标塔、古码头、授符井遗迹等重点考察。宋新潮指出,这两处重要遗迹,见证了中国海洋开拓事业的客观需要,催生了海神妈祖的历史过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物证和历史见证。贤良港是宋代莆田重要的商业贸易港口之一,可与我省著名的对外通商港口——泉州港相媲美。
对此,一些向来把贤良港妈祖文化和古迹遗存视为“造假”者耿耿于怀,大为不满。他们大会小会说三道四,发难指责,作梗搅局。
我们主张,历来百姓和学界共同认定:妈祖诞生港里、羽化湄屿,祖祠、祖庙同样神圣而并非一边真一边假,这何错之有?但编者刘、朱二位却硬要倒打一耙,把“强化莆田妈祖宫庙的讼争与内耗”,故意“打横炮”、“捣乱”、“破坏大局”,“心怀鬼胎的人故意捅漏子、搏出位”,“一粒老鼠屎”“沉渣泛起”,“扰乱公众视线”等等吓人的高帽,戴在我们头上,这些帽子难道“正合适”吗?我看正相反,还是不顾事实、颠倒黑白者,自己捡起来戴上吧——他们真的正好合适!
二、《湄洲是妈祖诞生地文献史料汇编》当真“明确无误”吗?
《妈祖诞生地文献史料汇编》(以下简称“特辑”),在蒋维锬先生汇编的《妈祖出生地史料辑录》66则基础上,成倍增补史料;貌似庞大,其实不过冷饭重炒,并无什么新意;并且,自行其是,各取所需,一边倒倾向十分明显。这样的“史料汇编”,怎么可能客观公正呢?
这么一本大且厚的所谓“认真梳理”的“特辑”,照样概念混淆,难以辨析。笔者2014年春在《妈祖研覃考辩·妈祖诞生地考辩》中,曾对蒋维锬先生所编的66则已作了全面、具体的阐述,这里再对增补本略加评析。
“特辑”第一編题记声称:“方志(130条)直指妈祖诞生于湄洲。……千余年以来,妈祖出生于莆田湄洲岛既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常识。”这是大大的夸大其辞。笔者粗略浏览一下,发现真正言及妈祖出生地的只有十分之一左右。诸如“母王氏生神于莆田湄洲屿”,“生妃于莆田之湄洲屿”等等;而绝大部分摘编,依然秉承蒋先生的老路,把妈祖的祖居地、籍贯、升天处、祠庙地址等,统统当成了出生地,并没有“直指妈祖诞生”地。例如“神居莆阳之湄洲屿”、“世居鯑山”、“莆田湄洲人”、“莆田湄洲屿林氏女也”、“神之故里”;“顺济庙,本湄洲林氏女,为巫”、“庙其故居地也”、“庙于湄洲”、“今建庙于湄洲”……其老调重弹,一脉相承,一成不变。不妨比较一下66则的一些记载吧:妈祖为“莆田湄洲人”、“湄洲山中之神女也”、“原籍莆田县湄洲”,“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炳灵于湄洲”、“天妃庙在湄洲屿”、“湄洲神人濯厥灵,朝游玄圃暮蓬瀛”……。
“特辑”中,还有些与出生地等毫不相干的史料,如第76则载(清)许鸣磬《(道光)方舆考证》曰:“湄洲屿,一名鯑山,有田数十顷,鱼米饶足。洪武初,都指挥李彝奏迁内地,虚其地。嘉靖末,总兵戚继光奏复。”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史料,只是简述了湄洲屿的一些史地情况,而且不少语句来自林光朝和《兴化府志》,内容并无一字涉及妈祖出生。如此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精选”,真让人莫名其妙而哑然失笑。
史料汇编或史学研讨,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概念明确,有的放矢。而这些记载,绝大部分与妈祖出生地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编者有意混淆概念以混淆视听,制造所谓“直指妈祖诞生于湄洲”的假象,继续误导读者与学界。
再说,所谓“千余年以来,妈祖出生于莆田湄洲岛既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常识”,更是痴人说梦。据我所知,所谓“妈祖是生于湄洲岛的渔家女”之类奇谈,只是1986年之后才出现的一家“偏识”,个别怪论——更遑论什么“常识”云云。
“特辑”“第二编碑文散文皆言神女生于湄洲”。这也是完全言过其实。例如第43码谢章铤文曰“妈祖在宋代祈晴祷雨,不独恩在矣”;董沛文曰“宋初莆田人也……庙于湄洲……羽化湄洲”。限于篇幅,不再过多赘引,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看看原文吧。
“特辑”中,还有些所谓“增补”者,其实是66则的旧料重复,如李俊甫、黄岩孙、陈让、康大和、黄仲昭、林尧俞、何乔远、陈琯、黄凤翔、徐观海、王必昌等人的史料;有的故意一分为几,拆少为多,虚张声势。既然编者自称“认真梳理”了,怎么就不加以仔细审核辨析?这样的粗疏马虎,又能得出什么科学、正确、令人信服的结论呢?
纵观“特辑”汇编不难发现,摘编者指鹿为马、以假乱真,常使用两大“法宝”——“魔幻等式”。仅仅举其两点来说。
其一,以偏概全,浑水摸鱼,硬将祖籍地全等于出生地。
祖籍地怎么会全等于出生地呢?古往今来,莆阳人勇闯天下,而不管他们出生于天南地北、国内境外,一般都会自称是“莆田人”。这说明,说自己是哪里人,籍贯何地,原籍何处等等,未必一定出生在那里吧。这点生活常识,就不再展开赘言了。
其二,强词夺理,将水搅浑。而故意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目的,就在于蒙蔽读者,欺骗学界。
编者一直强调:“湄洲、湄屿、湄洲屿,即今湄洲岛。”用数学语言表示,即湄洲=湄洲屿=湄洲岛;论者甚至进一步推论曰:“考诸史料,在莆田,‘湄洲’历来只是湄洲岛的专名,并无其它地域的指代”。也就是说,“湄洲”历来是湄洲岛的专有名词,专门指代。他们甚至强词夺理地提出,凡说“湄某”都是简称湄洲岛。“如此怪论”,真会使人笑掉大牙!
先说“湄洲”不等于湄洲屿、湄洲岛。
考诸史料,“湄洲”并非“历来只是湄洲岛的专名,并无其它地域的指代”。
宋元明清有关“湄洲地”的史料,比比皆是。请看以下4条权威典籍记载:
万历三十年前(1602)叶德辉编辑刊印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天妃娘娘》(其不少材料来自元代)载:“妃姓林,旧在兴化路宁海镇,即莆田县治八十里滨海湄洲地也。”
明·费元禄(江西铅山人,万历年间到过莆田)《天妃庙碑》:“天妃林氏,……旧在兴化军宁海镇,即莆田县治八十里滨海湄洲地也。”
明万历年间,福建晋江人、史学家何乔远所作《闽书》亦云:天妃“朱衣现光,遍梦湄洲墩父老。父老相率祠之,曰‘圣墩’。”
清·杨浚《湄洲志略·卷三》:“时时显神,遍梦湄洲父老,遂祠之,名其墩曰‘圣墩’。”
这“(圣墩)湄洲”、“湄洲墩”、“圣墩湄洲地”等,具体在哪里呢?
《天妃显圣录·圣墩神木》载:“莆海东有高墩,……号曰‘圣墩’”。
明代著名史学家周瑛,莆田沿海人士,他很可能亲临过圣墩,因此其《圣墩吴氏新建祠堂记》写得更加明白具体:“涵江之南,有地曰‘圣墩’,吴氏居焉。……七世祖念四府君迁徙圣墩。其地在平田中。有支海自上黄竿,逶迤西行,自屋后止。木兰、延寿二溪水,自前来注之。”(《兴化府分册·莆田县》第131码)
当代方志学者、律师朱金明等人在涵江实地考察后认定:“在确定了圣墩桥的所在,我们就有理由推断,所谓“宫后桥”,系指圣墩宫的后面,故俗呼“圣墩桥”为“宫后桥”。那么,圣墩遗址应当就在圣墩桥的南边,在宋时应属白塘李氏地界的莆田北洋中沟(陈桥沟)流入白塘处的高墩上。”(《妈祖圣墩祖庙何处寻?》)这与《兴化府志·桥道志》“圣墩桥”条下注引《宋志》:“承信郎李富建”,是相吻合的。总之,“圣墩”湄洲地位于莆田“涵江之南”,而并非近百里之外的湄洲岛。
有人可能困惑不解地质疑:怎么可以把距离湄洲屿近百里的涵江白塘圣墩也称作“湄洲”呢?蒋维锬先生生前对此就感叹道:“不明底里的后代人把‘湄洲’与‘圣墩宫’联在一起”,“明人费元禄、何乔远等亦认为如此”;而他自己“坦白地说:‘原因何在却弄不清楚’”。(蒋维锬《关于圣墩遗址问题的再商榷》)可以说,正是由于不明白“湄洲”概念之大小、变化,才使得蒋先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误读误判的泥潭。在他眼里,“湄洲”全等于“湄洲屿”;“神女生于湄洲”,就是“妈祖生于湄洲屿”云云。
可见,依多种史料明确记载,“湄洲”可沿海岸线向北延续至涵江港一带。
明确指出“湄洲”不等于“湄洲屿”的,还有明代著名史学家周瑛。
周、黄二位饱学之士,编撰完《八闽通志》,兴化知府陈效就请他们编纂《大明兴化府志》(《兴化府志》)。这部洋洋大观的地方志,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完成的。该书的学术性、权威性,都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部史书巨著的官方色彩也很浓厚。由于“自宋迨明,凡三百年”,莆田没有修撰地方志书。因此,周、黄二位是受兴化知府陈效的重托完成使命的。因而,《大明兴化府志》要数现存最早、最规范、最权威,最带有明显官方色彩的地方志。
《大明兴化府志》中,有一则直接谈及妈祖、湄洲屿、湄洲的——
湄洲屿海上岛屿,若湄洲,若上黄竿、下黄竿,与夫南日山,宋元以来居民甚多。洪武初,以勾引番寇,遗祸地方,守备都指挥李彝奏迁内地,岛屿遂虚。湄洲在大海中,与极了相望;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永乐间,中贵人曰三宝者下西洋,为建庙宇,制度宏壮,谓海上大获征应云。
由于这则明代的正规史料,对于判定妈祖诞生地极其重要。然而,又往往被人曲意解读。笔者参照《重刊兴化府志》第226-227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并核之1503年刊行的,二者文字完全一致。清•杨浚《湄洲屿志略》除开头几句外,文字也均相同。然而,“特辑”编者刘、朱二人采取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方法“改造”之。例如第8条把66则所称的作者周瑛,被改头换面变成了黄仲昭,并且略去了开头十分重要的15个字“若湄洲,若上黄竿、下黄竿,与夫南日山”,硬是“缩水”为:“湄洲屿,海上岛屿……宋元以来,居民甚多,洪武初,以勾引番寇,遗祸地方,守备都指挥李彝,奏迁内地岛屿遂虚。湄洲在大海中,与极了相望。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
这则史料文字虽然不多,内容却相当丰富,主要有三大要点:
1、说明湄洲屿跟在它附近的大岛,诸如湄洲、上黄竿(黄瓜岛)、南日山(南日岛)一样,同为“海上岛屿”。湄洲屿与湄洲,二者当时是彼此独立、大小比邻的两个“在大海中”的岛屿,所以跟“上黄竿,下黄竿,南日山”诸岛相提并论。66条和“特辑”编者引述时,却一再故意省略“若湄洲,若上黄竿、下黄竿,与夫南日山”等重要文字,使人不明了当时“湄洲”是跟“湄洲屿”一样的“海上岛屿”,为所谓“湄洲就是湄洲屿”埋下伏笔。
2、“湄洲在大海中”之前为句号,所以天妃“生于其上”的主语,则是承前省略的“湄洲”,而并非词语条目“湄洲屿”。笔者特地查阅了多个不同版本,文字完全一样!做为重要参照,清•杨浚1888年面世的《湄洲屿志略•山川》文字与之一字不差:“湄洲在大海中,与极了相望。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载《湄洲屿志略》卷一)由此可见,“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的,是“湄洲”,而不是“湄洲屿”。这一点区分十分重要,而且必要。
3、为了避免混淆,细心的老史学家周瑛进一步具体说明了这个“湄洲”(贤良港),是能够与“与极了(贤良港西面著名港口)相望”的比邻之地。贤良港西南方的山柄村(今妈祖阁所在地)曾经也是孤悬海中的小屿,靠沙洲穿越乌垞浅海跟吉了(极了)若即若离连接,涨潮时海水漫淹其间。在贤良港“沧海桑田”之前,“湄洲”与“吉了”之间,一东一西,一望无阻,彼此相对。史料中明确指出了此处的“湄洲”,是能够“与极了相望”者(地图直线距离5千米),因而并非位于吉了东南方的湄洲屿(二者直线距离10千米以上,中间还横亘着一座如今妈祖阁耸立的麒山,肉眼根本无法看到)。史学家的精明细致,更说明此处的“湄洲”,绝非“湄洲屿”。
可以说,明代邑人撰写的这则重要史料,大体上可以成为判定妈祖究竟出生哪里的“定海神针”,足以以一当十,一锤定音:“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其”铁定指代“湄洲”,而不是“湄洲屿”!
同为莆田沿海人的明代儒者朱淛,他在《天妃辩》中说得也很明确具体:“宋元间,吾莆海上黄螺港(贤良港唐代旧称)林氏之女”。这是最早指天妃为贤良港人的文献。
1960年12月,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向达校注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第一版),其142码载:“浮禧所……内是黄螺港,妈祖家”。词条注释更是明确说明:“浮禧所即莆禧所。天妃林氏相传家在贤良港,黄螺港即贤良港。”向达(1900-1966),曾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编委,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从刊》。
再说,编者刘、朱二位对清代陈池养(1788-1859)的史料,也只出现他1817年所说的妈祖“降生湄洲屿”之说,而对其晚年所撰的《林孝女事实》中改正的“海滨之人”,却只字不提,讳莫如深。这般“各取所需”的所谓史料汇编,哪是秉持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呢?
如今,“天下妈祖,祖在湄洲”已成为湄洲妈祖庙的最常见宣传用语。有的宣传品还振振有词地宣称:“妈祖出生于湄洲屿的理由确实充分……最早的史料都记载妈祖生于湄洲屿。据现有已知的66条记载表明,最早的史料都一致确认妈祖生于莆田县湄洲屿。”(见《天下妈祖祖在湄洲》小册子)问题在于,这个“湄洲”,并非单指或“专指”湄洲岛才是。“湄洲”,古往今来都不是专门指代湄洲岛的专称。此处之“湄洲”,绝非单个的“湄洲岛”而已,而是泛指涵盖湄洲岛在内的莆田海滨广大地域——包括核心区湄洲湾北岸、涵江圣墩、城郊白湖等,总共大约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大范围。
上述偷梁换柱、指鹿为马手法,“特辑”编者刘、朱二人还有一个“一了百了”的绝招:“逆我者亡”,直接封杀那些明显对其不利的史料。
试举年代最近的清代三则真正关于妈祖出生地的重要史料。
当年66条编者就特地说明:宋元明清除了林清标一条记载妈祖诞生贤良港外,其余“全部记载妈祖诞生在湄洲岛”。换言之,由宋至清,数百年间,只有一条史料记载妈祖诞生于贤良港。这不是大大言过其实了吗?“特辑”编者刘、朱二人也故意舍近就远,搜罗了不少边边角角、抄来抄去的方志记载,而偏偏“遗漏”了身边的省级石刻史料,以及著名邑人史学家编写重要县志。
其一,康熙五年(1666),清廷实行沿海“截界”,居民内迁。流寓在涵江凤岭一带的莆禧士民,为怀念故乡,自筹资金,在鉴前鼎建城隍庙,奉祀迁往涵江的莆禧城隍神。“越明年庙建成”,并取原莆禧“鲤江城隍庙”为庙名。其《凤岭鼎建鲤江城隍庙碑记》载:“遵海而西一里许,浦号贤良港。宋建隆初,天妃笃生于斯。”(收入《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215码,莆田人、厦大教授郑振满等编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莆禧城(福建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敕封守御城隍大神碑文》所载与之完全相同。因为涵江凤岭居民原本就是忠门鲤江(又称禧江)的截界移民。
其二,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张琴,于1928年前后撰写《莆田县志》(近年由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可以说,此书稿是明弘治《兴化府志》后,莆邑最权威、最重要一部史乘,较前人增添了不少新东西,使得记载更加具体、翔实。诸如《卷十八•坛庙》载明:“神林氏……生于莆禧港。”其《卷五•山川》条载:“贤良山:为安乐里左一支,由琼山发脉,横列三峰,曰螺峰、狮峰、象峰。居民数百家,宋圣女林氏天后故宅在焉。螺峰之阳有圣井,即天后窥井得符处也。”
其三,无论明末的《天妃显圣录》,还是清代的《天后显圣录》《敕封天后志》,都一致收入的《萑苻改革》(意为“草莽流寇洗心革面”),虽然标题、文字略有不同。它是最直接、最确切阐明东海之滨、湄洲湾畔的贤良港,乃是天妃“神灵梓乡”和“父母之邦”的——
明天启乙丑戊辰(1625、1626年)间,萑苻草寇李魁奇出没南溟,结伙入吉了抄掠;复迤逦到贤良港。港人拥神像江(海)头,示以神灵梓乡,冀免扰害。神乃显梦于酋长曰:“而焚掠了城,为祸酷烈,今尚欲困吾父母之邦,若不速退,将歼尔类!”……
三则史料,均白纸黑字,言之凿凿。这三条史料,笔者2014年春在《妈祖研覃考辩·妈祖诞生地考辨》中就引述过,编者刘、朱二人是故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们不禁要问:编者刘、朱二人声称他们是“把历代学人有关湄洲是妈祖出生地的各种文字记载摘录出来,以正视听”,但为什么视之若洪水猛兽,一味回避?史料编者刘、朱二人真的是一无所知,还是明知故犯,刻意要长期隐瞒之?
三、造谣污蔑,人品低下。
更为拙劣的是,编者居然公开造谣生非。他们胡说我说“湄洲”可指代“莆田全境”、甚至于“莆田全市”;并且进而加以冷嘲热讽:“我们感到如此以今律古,还敢摆出一副名师架子,实在有辱斯文。但凡思维正常者听了如此怪论,都会哑然失笑!我们不禁要问此君怎么连常识都不懂,连逻辑都不顾?”这是“好为人师者”炮制的“釜底抽薪的阴招”……
为此,笔者将2012初稿的《妈祖诞生地考辨》中有关解说“湄洲”的三部曲摘录如下,供广大读者客观评判——
首先,追根朔源,从文字学上“顾名思义。所谓“湄”,《尔雅·释水》和《说文》均曰‘水草交为湄。’《传》正义曰:湄是水岸。……也就是说,凡属水草丛生的水岸,‘水中的陆地’,甚至‘大陆及其附属岛屿’,皆可总称为‘湄洲’。”
进而推延说明“广义的大湄洲之地,涵盖湄屿在内的莆田海滨——包括湄洲湾北岸、城郊白湖、涵江圣墩等一个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
末了推论道:“面对这水光潋滟、水草茫茫的土地,以何相称最为恰当呢?有宋以来,莆邑最具知名度、最响亮的品牌,莫过于湄洲妈祖了。因此,以‘湄洲’统称之,确实是名正言顺,名至实归。这一点,只要想一想现在莆田市的报纸取名《湄洲日报》,莆田市社科联刊物取名《湄洲论坛》,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后者是泛指更广义的“湄洲”以代表全市。”
不料,这些简单明了的文字,竟又被编者刘、朱二人别有用心地歪曲了。面对如此拙劣得可怜可笑的阅读能力,我倒要反问:这应该就是逻辑学所说的,故意将对方推到一个明显荒唐可笑的地步,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是公然造谣污蔑,还是正常学术辩论呢?
笔者还要进而责问一句:学术争论,在于就事论事。编者胡搅蛮缠,硬要扯上本人的教师职业横加嘲讽,道德何在?这不才是“实在有辱斯文”吗?笔者以为,“名师”荣誉,是政府授予、社会承认的,要知究竟,上网一查便知;个别人有什么资格对此说三道四、品头论足呢?
编者刘、朱二人还借已故的蒋维锬先生说事,指责我“用无礼甚至是侮辱的语言攻击坚持妈祖出生‘湄洲论’真理的已故著名妈祖文化学者蒋维锬先生”,“借“学术争论”来诋毁往生者”,是“老而猥琐”等等。
此类责备屡有所闻,但我问心无愧故心安理得,不予理睬。既然编者再一次翻老账发难,本人不得不多说几句以正视听,澄清是非曲直。
对于已故的蒋维锬先生对于妈祖文化研究的功过得失,我在《妈祖研覃考辩·后记》已有比较全面、具体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于任何人,不管生者、逝者,都应一分为二,理性评价。针对编者指责,我这里只想再现过去的批评,看看究竟是否什么“用无礼甚至是侮辱的语言攻击”、“诋毁往生者”云云。
我说过,“从研究和传承妈祖文化层面来说,蒋先生的功劳和成绩是明显的”,可谓在其位而谋其政;但终其一生,在妈祖文化的一些基本点上(例如妈祖出生地、家世身世、妈祖封号不包含“天后”、褒封“天后”是乾隆二年等等),蔣先生始终存在误读、错判和误导,“往住又给历史披上重重叠叠的面纱,令人难识庐山真面。而只有拨开迷雾,正本清源,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蒋维锬《“妈祖”名称的由来》)
尤其是蒋先生去世后,一些人出于各自目的,对其进行了不少欠恰如其分的过誉评价。诸如:赞扬他是“妈祖文化研究的拓荒者与导航者”,“他为让湄洲走向世界,让世界朝圣湄洲做出巨大的贡献,堪称‘大陆妈祖研究第一人’、‘妈祖文化之先驱’”,“我们失去了一位慈父般的良师,妈祖文化事业失去了一位可敬可歌的文学巨匠”;“我们失去了一位旗手,一座标杆。蒋先生的仙逝无疑是妈祖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就像该领域内的超强地震”。“他的学术态度极其严谨”、“他满腹经纶,厚德可风”,“博古通今”、“淡名薄利,堪称一代宗师”,“这种由学养滋润出的‘仙风道骨’般的气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我想,即使蒋先生重生再世,恐怕他也会恭谦地再说一遍:“对此赞誉,实不敢当”!
对于蒋先生,本人一是匡正其论述的误讹之处,二是提出评价应当客观公正。难道这样就是“用无礼甚至是侮辱的语言攻击”,“诋毁往生者”?编者刘、朱二人无端给我扣上“侮辱的语言攻击”、“诋毁”等大帽子,能否举出一些实例?否则,笔者就要指控他们对我进行“侮辱的语言攻击”和“诋毁”!
编者似乎是在为尊老敬贤大鸣不平,其实不然。《读出历史的真相》大言不逊地指责道:“最近有两位莆田退休的所谓专家写成了《妈祖的足迹》新书,拉一位莆田老市长作序,实欲借老领导来‘垫背’,为港里‘妈祖的诞生地’造势与代言。”“垫背”何意?辞书曰:“人死后在屍身下放置财物。今比喻使别人为自己分担过失或罪责,或代人受过或陪人受罪的人。”吴先生是位口碑甚好的莆田市原市长,后任省农业厅厅长;吴先生还是一位知名的作家。编者刘、朱二人居然使用“垫背”之类的谩骂性言语侮辱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老市长序言中并没有所谓的“为港里‘妈祖的诞生地’造势与代言”,而只不过秉公说了句公道话:“妈祖,一位名垂千古的女神。公元960年(农历)三月廿三日诞生于贤良港,公元987年(农历)九月初九在湄洲岛羽化登仙。”因此“得罪”了编者刘、朱二人,所以“惹祸上身”,遭受无妄之灾。
编者刘、朱二人不仅对老领导不恭,而且对主流媒体央视和著名学者发表的不合己见的论述,同样肆无忌惮地进行嘲讽攻诋。文中,他们对央视《敕封天后志》是“经朝廷敕封得名”评说大为光火,讥讽这是“拾人牙慧”,“其说不但危言耸听,而且此种解释更是可笑至极,连‘敕封天后志’竟都可作如斯曲解。”“说到底可能为某种利益所驱使,他才会如此挖空心思,……罔顾史识,强作曲解。……贻笑大方事小,贻害无穷则事大。”
2010年11月23日,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4套)首次播出林清标和《敕封天后志》的视频,时长2分半;2011年5月3日,中国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9套)《方志中国》栏目,再次播出林清标和《敕封天后志》的视频。此次是以志书形式介绍《敕封天后志》,时长近7分钟。其中有央视和社科院学者叶涛的点评:“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莆田举人林霈,任台湾凤山县教官。当时台湾府开始兴建妈祖天后宫。而自认是妈祖后裔的林霈觉得,仅仅修建几处祭祀场所,似乎还不足以让台湾民众真正了解妈祖。于是林霈决定,在台湾传播妈祖文化,但他手头并无资料,只好向在福建莆田老家的父亲林清标求助。林清标在考察搜集妈祖的生平事迹后,编撰了《天后志上·下》两卷,上呈朝廷,经朝廷敕封,得名《敕封天后志》。志书包括了妈祖的生平事迹、神迹传说、历代皇帝敕封等内容,不仅让台湾民众全面认识了妈祖——林默,也成为今天了解妈祖文化最权威的文献。”
综上所述,足见编者刘、朱二人不仅文品拙劣,而且人品低下。借用他们自己所言:“若良心未泯,应改弦更张,从此不应再说胡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