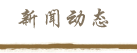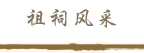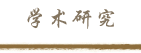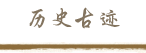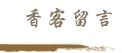人气排行榜
“南溪草堂”绝非南溪亭
2017-01-05 责任编辑:贤良港 我来说两句
|
——《天妃显圣录》首序诞生地考正
“南溪草堂”是明代尚书林尧俞整理《天妃显圣录》,并写作首序的瑞圣之所。明天启五年(1625),因不满宦官头子魏忠贤弄权乱政,林尧俞愤然回乡。归来之后,他在莆田莒溪溪南村外5里筑“南溪草堂”(如今九龙谷景区内),以与友人觞咏赋诗为乐事。归隐期间,林尧俞欣然书写了他一生中最为璀璨的一笔——编纂《天妃显圣录》母本,并挥笔作了首序。他满怀深情地写道:“余自京师归,偶于案头得《显圣录》一篇,捧而读之,不觉悚然而起曰:天妃之英灵昭著有如是乎!……惜乎显圣一录,尚多阙略。姑盥手而为之序,以俟后之釆辑而梓传。”
第二年“暮春”,年迈体弱的林尧俞亲自携带编纂整理之后的《天妃显圣录》母本,乘坐“巾车”(古代一种有帷幕的车子),从贤良港渡海登上湄洲屿,亲手交给祖庙住持僧照乘(《天妃显圣录》林兰友序:“昔大宗伯林公手授一篇”)。他还即兴写下《湄洲屿》一诗,表达欣慰之情:“暮春命巾车,言憩湄之涘。徘徊芳树林,夕阳已在水。……鲸波几时平,渔歌处处起。”当年十二月初七,林尧俞去世。
然而,380多年过去了,对于“南溪草堂”的确切地址,近现代莆田文史界看法不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南溪草堂兴建,到主人林尧俞去世了,头尾仅仅两年,真正的亲历者、目击者寥寥无几。所以,其具体地点,也随即很快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莆田史乘不见明确记载,林氏族谱也没有丝毫痕迹。242年前,即清乾隆年间邑人郑王臣在《莆风清籟·兰陔诗话》中感叹曰:“吾乡前贤归田后,多筑郊墅,如郭尚书(应聘)之钟潭,曾侍郎(楚卿)之棠坡,彭侍郎(汝楠)之柳桥,林尚书(尧俞)之南溪”,而今“几何不复,为荒烟蔓草乎”!可见“南溪草堂”当时就已经完全荒圮,不复存在了。
后人对南溪草堂遗址的猜测不少,但几乎都是非亲历者望文生义的主观臆断,因此留下了一桩历史迷案,成为妈祖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缺憾。
仅有的“南溪草堂”若干亲历者的诗文集长期流失异地,难得一见。例如,张燮的诗文集《群玉楼集》大陆就很难寻觅。而张燮所写的有关林尧俞(咨伯)和南溪草堂的诗文、书信等,统统被“束之高阁”,莆田学者未曾得见。
今年,在同窗好友陈庆元(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导,历任福建师范大学古籍所所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文任等)、台湾博士严文志的真诚帮助下,笔者终于有幸见到《群玉楼集》(清刻本复印)的相关诗文,随之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这篇短文,意在与广大读者分享我的探实结果。
張燮诗句一锤定音
张燮(1574—1640),字绍和。福建龙溪人,出生于官宦世家。他天资聪慧,10岁通五经,兼览史鉴百家。年轻时,文章诗歌名噪一时。张燮20岁中进士,为人志趣高雅,豪放博学,广交海内名士,与黄道周、徐霞客、何乔远、林尧俞等学者名流交往甚密。张燮一生著述、编纂的著作有15种共约700卷,黄宗羲称他为“万历间作手”。其著作除著名的《东西洋考》外,还有《群玉楼集》八十四卷,《闽中记》等。
做为林尧俞的挚友,張燮多次旅游莆阳,而且曾“过莆阳在南溪一宿”(《答林咨伯祭酒》),并且留下十分重要的《访林咨伯南溪留酌即事》:“涧曲峦危一草堂,亭台无数抹新妆。寒流溅瀑微闻籟,晚菊环英漫散香。客到蹲林云作供,僧归扫石薜为裳。扶筇欲遍游仙路,岭背斜穿径许长。”全诗短短56个字,却蕴含着诸多信息,包括关南溪草堂的珍贵线索(周围及附近环境)。
历来有关南溪草堂所在地的争议,共同点是它比邻寺院,而分歧焦点在于:它究竟是广化寺,抑或宝峰寺?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应主人林尧俞邀请,“留酌”南溪草堂的张燮的“僧归扫石薜为裳”,足以成为解开这一历史谜团的金鈅匙,使得“铁板钉钉”,尘埃落定!
其一,提供了南溪草堂的地理大环境。这“涧曲峦危”却又“亭台无数”的“草堂”之地,应该坐落于群山之间的小盆地。莒溪溪南村宝峰山之下,正好有一片好几十亩的土地(原先它还属于未被拆毁的宝峰禅寺产业)。【《群玉楼集·聞少保林公咨伯之訃未遑絮酒哭以輓章》,也有“绝壁松云峻,重霄苇露开”、“惜矣南溪瀑,怀哉北海杯”等,可以佐证】。其众多“亭台”,应该包括宝峰寺院建筑,以及“留云阁”等等。林尧俞去世不久,其至交何乔远修订的《闽书·林尧俞传》载:“家园结留云阁、南溪草堂,拉名缁胜侣(指僧人)其间,染翰赋诗以为乐事。”也点出了所在地的明显特征:一是南溪草堂附近有个留云阁——它应该即林元霖《南溪》诗中所吟的“看云溪阁坐来孤”;二是距离寺院很近,可以常与僧人赋诗唱和。再则,南溪草堂四周“寒流溅瀑”、林密云绕(蹲林,坐在树林之下。《广韵》:“蹲,坐也。”《说文》:“蹲,踞也。”)
其二,此地临近“游仙路”,而又有“许长”距离,且当年须翻山抄小路从“岭背斜穿”前往(约30分钟路程),这是写实。相传在汉武帝时,有何氏九兄弟在九鲤湖炼丹济世,丹成跨鲤成仙,九鲤湖因此而得名。九鲤湖景区以湖、瀑、洞、石四奇著称,她与武夷山、玉华洞并称为福建“三绝”。九鲤湖是一个天然的圆形石湖,直径67米,平均深度15米。“九鲤飞瀑天下奇”之美誉,说明其最引人入胜的是九飞瀑,总落差432米;按落差分九漈,徐霞客盛赞“峻壁环锁,瀑流义映,集齐撮胜,惟此为最”。南溪草堂附近就有属于莆田地域的石门漈、五星漈、飞凤漈、棋盘漈、将军漈等5漈瀑布。石门漈为九鲤湖的第五漈瀑布,九漈瀑布中最宽的一漈,有“小黄果树”之称。五星漈在石门漈下游约一公里处,为鲤湖第六漈。飞凤漈为鲤湖第七漈,棋盘漈为鲤湖第八漈,将军漈为九鲤湖第九漈。漈的尽头有两座石崖,高高矗立,状如武士挡关,雄伟异常。两岸危峰列嶂,林木葱郁。鲤湖之水奔流至此,宕落而下,注入莒溪。
其三,也即最紧要、最令人击节称赞的是“僧归扫石薜为裳”,此句一清二楚地表明,南溪草堂与某寺院近在咫尺,因此酌饮时抬头举目就能看见僧人在薜萝或薜荔之下打扫石径(薜衣、薜户,古指隐者)。如果南溪草堂真的就是广化寺后3里处的南溪亭(所谓“南溪亭者,即南溪草堂也”;“南溪草堂又称为南溪亭”)——也即1千多米外,怎能凭借肉眼看清此番情景?何况,广化寺与南溪亭之间,还并非一览无遗的“一马平川”,其间山路崎岖,拐弯曲折;而宝峰山山腰的宝峰寺跟山脚下的南溪草堂,直线距离仅区区两三百米,望之当然历历在目啦!真可谓此寺非彼寺,此僧非彼僧也。两者不能“移花接木”,更不能指鹿为马。
为再做考证落实,日前笔者特地驱车到广化寺后几里的“南溪岭”之“南溪亭”。从水泥公路沿老石径(城里通往莒溪、华亭之古道)下去几十米,只见小小的南溪亭,静静地呆在繁杂的草木间。入内勘察,其大小大概只有十几平方米;除了壁画的山神和供案外,一无所有。这能是林尧俞归隐的住所,并且是“拉名缁胜侣其间,染翰赋诗以为乐事”的场所吗?“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释名·释宫室》),主要就是供人歇脚的。南溪亭旁两棵硕大浓密的榕树,诉说着它古往今来“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功用。立足南溪亭四周眺望,其间山路崎岖,拐弯曲折,压根儿见不到广化寺的踪影——遑论能看到寺僧扫地!
由此,我进一步坚信:南溪草堂绝非“就是”广化寺后面3里的南溪亭,而是在常太溪南村附近的宝峰山下。
当然,南溪草堂地址的考证,除了亲历者的诗文之外,林尧俞其亲友的诗歌,也是必不可少的依据。下面,我们也摘要观之。
林尧俞《南溪》二首
才得名山便卜居,况兼云水称樵渔
自知邱壑生来相,好读神仙方外书。
旧堰废塍依作沼,松萝藤蔓葺为庐。
鵁鶄溪上闲相傍,城市庞公迹渐疏。
斜风细雨半春朝,濯濯新栽嫩柳条。
地迥谁留莺不去,人闲兼喜鹤能调。
松花饷客过寒食,筇竹寻僧度野桥。
试问云芽今茁否?龟山此路不曾遥。
林尧俞《莒溪》
深山行欲尽,平楚忽苍然。
木末饥鼯走,沙头浴鹭眠。
开篁朝饮水,蕴火暮烧田。
遥识临溪者,农谈坐树边。
从诗的内容看,特别是末尾两句,显然他不是以匆匆来去的游客路人的身份落笔的,而是充满近邻熟人的亲切感。虽然林尧俞致仕后在“深山”中的南溪草堂才度过短短两年光阴,但因其平易近人,还是使之结识了不少“临溪者”(甚至可“遥识”之),赢得了许多“农谈”朋友。
除了上述林尧俞的《南溪》二首外,再请看明万历年间,莆田人林廷润(字寄苍)笔下的《南溪草堂》:
柴扉半掩杜陵家,门对红泉浣落花。
鹿苑僧谈方外果,龟山人送雨前茶。
一泓新水添春涨,几点飞禽拂晚霞。
地肺居深情自远,天心静见思无涯。
如果还嫌地域特征不够鲜明,再请看以下几首诗吧:
林元霖《南溪和家兼宇(尧俞)宗伯韵》
溪南猿鸟讵孤他,惊世勋名赋涧薖。
五载青山频梦绕,百年黑发尚头多。
古松流水闻棋响,绝磴悬崖见鹿过。
更爱石门新受月,满窗凉影写垂萝。(原注:宗伯有“孤他猿鸟怨山家”之句)
林元霖《南溪》三首
流泉泱泱触溪鸣,峰顶遥听急雨声。
旧插野松皆过屋,新开绝嶂已通耕。
一封春茗披青箬,万壑秋涛泻白罂。
昨日留僧诗未和,晓来也有事关情。
野坐桥西日夕频,飞泉远远溅乌巾。
得闲风月真成主,无恙溪山解待人。
时向云间看鹤纵,多于醉里觉诗神。
凭他兜子来还往,谁识尚书自在身?
看云溪阁坐来孤,半点曾闻世事无。
短睡多怜山鸟唤,闲行不待众人扶。
沽来薄酿邀僧醉,减得午餐与鹤俱。
夜久一灯微竹屋,静听冷灶鼠巡厨。
林元霖,字伯珪,莆田县人。明崇祯丙子年(1636)举人、孝廉,罗田知县,著有《雪竺集》。
林元霖《南溪和家兼宇宗伯韵》首句“溪南”一词最吸引眼球,因为它实际上已经点明了“南溪草堂”的具体地点——常太莒溪至今仍有“溪南村”、“溪北村”。从律诗的平仄格律看,“南溪”“溪南”皆为平平,而林元霖在诗题中简称南溪草堂为“南溪”,首句则点明其地名乃“溪南”,概念十分明确,区分清晰。“草堂”,原指草屋。文人称其所居为“草堂”,含自谦卑陋之意。后来,一些志士避世避乱,筑室隐居,亦号“草堂”。据统计,草堂命名,未必都是“地名+草堂”。
为了更加明确溪南村、南溪草堂一带的地理环境,请再看看下面几首明代诗歌。
黄顺吉《游南溪草堂》(集句二首)
石门斜日到林邱(杜甫),细草春香小涧幽(韩翃)。
明月苍苍风瑟瑟(白居易),青山历历水悠悠(张元昌)。
还将石溜调琴曲(李峤),折取花枝当酒筹(白居易)。
圣代即今多雨露,(高适),白云何事欲相留(刘长卿)。
桃源四面绝风尘(李绅),乞得归来自在身(王建)。
灵断竹溪无别主(卢纶),始知城市有闲人(许浑)。
桃花细逐杨花落(杜甫),竹色初明水色新(白居易)。
借问欲栖珠树鹤(李白),江潭何处是通津(耿湋)。
黄顺吉,字吉甫,号梅岩,莆田人,明万历中布衣,有《集美诗稿》。
还有,明万历诸生方应侁(字行渐,有《青溪草堂集》)《南溪》诗云:“名山荒落已多年,选胜重开别洞天。凿破红泥成翠壁,疏迴碧沼汇清涟。旋烧茶鼎逢僧话,闲聚花茵借鹿眠。就此一区堪避俗,何须更觅买山钱?”
上述几首林尧俞同时代诗人(有的还是宗亲)的作品中,从地形地貌看,“石门”、“悬崖”、“绝嶂”、“万壑”等等,均是“广化寺后两里许”无法见到的;而常太镇境内有大小山峰106座,最高的古山尾海拔832.6米。许多地名与古寨遗迹相连,如南山寨、太平寨、鼓旗寨、石狗寨、酒池寨、朝天寨等,各个寨堡残基尚历历可见。“石门”、沟壑、“悬崖”、“绝嶂”更是随处可见。
再从典型景物观察,上述诗中频频出现的“猿”、“鹿”,可谓极好的“标志性景观”。笔者查阅了百来首古人,尤其是明清人咏广化寺的诗词,无一写到“猿”、“鹿”——可想而知,络绎不绝的香客,日夜鸣响的钟鼓,早已教它们退避三舍了吧?无论如何,距离广化寺二三里,未免太靠近市区和人烟了(即使在明代),不符合那些诗中所描述的景物。
相反,写常太里、九鲤湖(溪南地处鲤湖以下,实际上与鲤湖有着不可割舍的“一体化”关系)的古诗中,却一再出现“猿”、“鹿”;甚至“猿”、“鹤”两种意象连用的,也比比皆是。诸如“石芝肥野鹿,崖蜜割山僧。”“桥边有路鹿相引,洞口无人花自开。”“山间猿自啸,松老鹤犹还。”“清秋雨歇猿听惯,静夜风高鹤睡迟。”“崚嶒石壁猿声外,潋滟山泉鹤唳中。”“鹤唳湖天寂,猿啼鸟道寒。”“猿鹤避人何静便”……
从动物食物链(生存条件)的角度考察,它们都是老虎的美食。莆田山区、沿海直至民国期间还常有猛虎伤人。九龙谷附近就有名曰“虎堀山”者。“堀”通“窟”,即山上有老虎的洞穴也。总之,诗歌成为“南溪草堂”极好的实地“录像”与探寻向导!
“南溪草堂”,关键在“溪”
林尧俞把自己的诗文集取名为《溪堂文集》、《溪堂诗集》,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他晚年是临溪而居的——这才与“南溪草堂”珠联璧合、彼此呼应。
林尧俞《南溪》诗称“鵁鶄溪上闲相傍”、“筇竹寻僧度野桥”;林元霖《南溪》诗中“溪鸣”、“溪阁”、“桥西”等等。明朝至今,不过数百年时间。期间,莆田地域并没有出现沧桑巨变,基本上山川依旧。原宝峰寺下的那条从九鲤湖流向莒溪的大溪,水面大多三四十米,大水时可达百米。桥上有几座石桥;而“去凤凰山三里”,古今均不存在溪流。笔者有幸采访到几位现年70岁上下的老人,其中有个还当过城郊一带的女挑山工。他们讲述了年轻时从城内十字街,步行前往广化寺(俗称上香路)的情景:全程大约6华里。广化寺后山一带是崇山峻岭,幽壑深涧,根本见不到什么大溪流。其自然景色,与何乔远转述的相一致:乱山中,两岸如削,有泉有潭,但并无大溪流。可以确认,古今广化寺方圆两三里之內没有任何大的溪流。谁想“望文生义”地在此地寻找南溪之水,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不信,请迈开双脚,亲自到广化寺四周踏勘一番吧。近日,笔者特地又到广化寺后树木丛生的南溪亭实地考察一趟,还登上岭头举目四望,哪有什么溪流、瀑布的踪影?而且,站在南溪亭四周眺望,根本见不到广化寺的影子——遑论还能看到寺僧打扫石径!
龟山茗茶,重要之参照物
上述诗歌,还有一个不约而同之处:提及品尝龟山“春茗”“云芽”。诸如“龟山此路不曾遥”、“龟山人送雨前茶”、“一封春茗披青箬”、“旋烧茶鼎逢僧话”呢?林尧俞《春园杂兴》二首:“蓬门一径远,茅屋数间斜。得雨新移竹,分泉细校茶。山僧来隔寺,术(同“秫”,黏高梁)酒饷邻家。”“钟声知寺近,燕语觉春迟。水石攒苍耳,阑干长灵芝。”瞧,又是梵鈡“寺近”,“山僧隔寺”,“分泉校茶”!
龟山古名龟洋,又名龟洋山,位于市区以西15公里的城厢区华亭镇境内。因山形隆起似龟背,毗连的紫帽山昂立如龟首,故名。唐长庆二年(822年),无了禅师来龟山开山,辟茶园18处。明代扩建为寺。龟山,雾浓露重,气候阴凉,盛产茶叶。明朝万历时有名茶“月中香”,定为贡品,年产数百担。而“南溪草堂”存在的17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月中禅师与陈经邦等募捐重兴龟山寺之时,当时住寺僧人达500人之多。如今龟山产的“炒绿”,依然色泽碧绿,香气浓郁,列为外销名茶。
南溪草堂距离龟山寺十里左右,而广化寺距离龟山三十里上下。所以,既便于常喝龟山茗茶,又易于与宝峰寺僧赋诗唱和的,只能是宝峰寺下的南溪草堂,而不是几十里外的广化寺。
南溪草堂遗址的涉足者,目前见诸史册的仅有一人,那就是清代的俞荔。俞荔《迂溪草堂初成》诗中描述的关键有两句:“是非难染溪边石,……却忘身在万山中。”(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七)沈德潜还简介道:“硕卿居官清正,以失上官意落职,到家后,杜门自守,筑堂曰迂溪,犹柳子自愚,而并愚其溪也。”显然,它是远离城市、“翛然绝俗”的“万山中”,并且是在“溪边”!此山、此溪,绝非在莆田郡城几里的近郊——俞荔自云“我爱庞德公,足不蹈州府”!
俞荔,字硕卿,号果亭,晚更号峚山,莆田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官长宁知县。据张琴《莆田县志》载:俞荔“廉,……归田行李萧然,……欢结茅南溪授徒。……筑迂溪精舍,匾以遗人。自题云:‘柳桥归棹无他事,笑看迂溪树树花。’”俞荔生前挚友郑王臣在《莆风清籁集》俞荔之《兰陔诗话》云:“峚山翛然绝俗,晚年究心释典,结茅山中,罕至城市。诗如其人,冲淡无烟火气。”
从张琴、沈德潜介绍可知,俞荔“结茅南溪授徒”之“迂溪草堂”,即当年林尧俞筑“南溪草堂”之南溪。
顺便提及,偌大一个莆田,林尧俞之所以选择莒溪作为归隐居所,也许有这么一个因素:其先祖曾经居住常太莒溪(参见《莆田市姓氏志》第52码,方志出版社,2010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后,林尧俞曾以服丧、避祸等理由,“居家二十余年”。其间,尝促使开通修复自莒溪直达九鲤湖的观光小道,方便游人观瀑。
总之,“南溪草堂”必须具备3个充要条件,或曰参照物——溪流(溪南村外虎堀溪)、寺院(宝峰寺)、龟山茶,三者缺一不可;而全然合符条件者,只有莆田莒溪溪南村这一处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