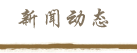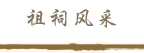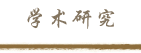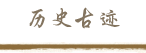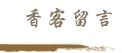《是“垂慈笃祜”,不是“垂慈笃祐”》驳议
2017-01-08 责任编辑:贤良港 我来说两句
|
《是“垂慈笃祜”,不是“垂慈笃祐”》驳议 ·许更生[文] 清嘉庆五年所加之妈祖封号,究竟是“垂慈笃佑”还是“垂慈笃祜”,争论已久。经历清末、民初“八千麻袋事件”的惨痛折腾,迄今连康熙年间敕封妈祖天后的正式档案文件也找不到了;而且,清代多次妈祖封号之原件“迄未发现”。因此,嘉庆朝之妈祖封号,也一直莫衷一是,成为一桩尘封的谜案。 使得问题复杂化的是,由于某种目前未知的原因,清宫档案有关嘉庆五年的妈祖封号,也存在“佑、祜”二说,以致清代文档也常有出入。例如,光绪年间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以及军机处的一些文件摘录,如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和咸丰三年(1853)七月,行草所书“垂慈笃祜”云云。 不过,劫后幸存的清宫档案中,还是有几次关于嘉庆年间的妈祖封号的记载。其中唯一一次正楷书写的奏章,见诸咸丰七年(1857)七月,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为“垂慈笃佑”云云。一般来说,楷体书写的文件,最为严肃端庄,也最不容易出错;再则,此份奏章乃两位朝廷封疆重臣——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建巡抚庆端联名跪奏之“原奏折”(该文本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4家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305码)。 然而,刘福铸《是“垂慈笃祜”,不是“垂慈笃祐”》一文,却提出:“‘垂慈笃祜’见诸清廷军机处的校正重录稿,其权威性要高于王懿德的原奏折稿,与楷书或行书字体无关。” 试问,难道两员封疆大吏以正楷书写、并且联名上奏的“原奏折稿”,其可靠性、“权威性”,反而不如朝廷办事机构办事员用行草字体匆匆“抄录”的文字(文稿中还有明显涂改之处)?再说,军机处权势再大,恐怕也无权“校正”更改大臣的正式奏章吧——何况事关天后封号? 其次,刘文还提出:“当事人赵文楷《槎上存稿》集中的资料最为可靠。按其书有多种翻刻或重排本,其中最为可靠的版本是赵文楷的个人专集《石柏山房诗存》”。 由于清宫档案中,内阁拟定并经嘉庆朱笔确认的封号批件,至今不见踪影。为此,蒋维锬先生在《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档案卷》相关“校记”中特地按曰:“有关内阁奉旨拟撰封号的档案,迄未发现。但赵文楷《槎上存稿》有《加封天后‘垂慈笃祜’四字,命臣文楷于福州致祭,礼成恭纪》一题,可证此次所加封号为‘垂慈笃祜’。” 此话说得明白:嘉庆皇帝给妈祖添加的褒封,正式档案文件“迄未发现”,因此编纂者只能凭借一首有关诗歌的题目,来加以判断并且认定的——“可证此次所加封号为‘垂慈笃祜’”。如此“移花接木”却自以为其“最为可靠”,对于史学研究,未免过于粗疏了吧。 照理说,有关事件重要当事人的诗歌,可以做为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问题在于,古往今来,赵文楷这首诗歌的题目,本身就存在两种不同版本,并且就是“佑、祜”之异。因此,怎能以之作为准绳,来确定一个重要的封号呢? 其实,古今刻印工都是人而并非神,可能误认错抄误刊。此类事不胜枚举。同样,从古到今,从纸质版本到网络版本,赵文楷那首诗题均有两个版本,例如《石柏山房诗存》与《清代琉球纪录集辑》等十二种(清•张学礼、王士祯等撰,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92种,1971年5月出版),就是其不同代表。台湾版所载赵氏《槎上存稿》,特地说明“据《太湖赵氏家集丛刻》”,其中诗题便为“垂慈笃佑”云云(台湾大通书局印行的《台湾文献丛刊·清代琉球纪录集辑》第98码同之,为“垂慈笃佑”)。 诗题本身相左,当然不足为据。笔者再举三个大陆出版社当代的典型事例。 1990年,蒋维锬编校、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妈祖文献资料》,也选入赵氏该诗,其第268码为“垂慈笃佑”;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妈祖诗咏辑注》(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所、莆田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合编,刘福铸、王连弟主编,蒋维锬副主编)选注该诗,其第294码也为垂慈笃佑”;而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妈祖文献史料汇编·诗词卷》(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所等编,蒋维锬、刘福铸辑纂),同样选注了该诗,其第257码却为“垂慈笃祜”云云。几乎相同的编纂者,有的仅隔两年,却连诗题也弄不清了,岂可以之为据? 从咸丰七年(1857)此后30年,清光绪十四年(1888)——也即敕撰的《钦定大清会典则例》颁布的第二年,福建著名文史家杨浚在《湄洲屿志略》(清光绪十四年木刻版,福建师大图书馆藏书)之“封号”、“祀典”、“奏疏”等篇章中,5次(分别见诸第39码、75码、76码、124码、130码。无论作者还是刻印工,总不会连错5次吧——何况书中文字笔笔清晰),根本不存在刘文所谓的“‘佑’字,撇画很短,与‘祜’极相似”,“可解释为杨浚误书或手民之误刻”云云(因此,《妈祖文献史料汇编·著录卷·湄洲屿志略》统统私自将“佑”字篡改为“祜”)。这里,不妨借用刘先生的一句话:凡是对论点不利的材料,“作者往往加以隐瞒以蒙蔽不明真相的广大读者,我们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换言之,杨浚《湄洲屿志略》中的嘉庆五年妈祖封号“垂慈笃祐”,与咸丰七年的清宫档案正楷书写的重臣奏章完全一致,一字不差!作为严谨勤勉的史学家,为了落实妈祖之九牧林家世,他亲自来到贤良港,仔细考证了天后祖祠神位牌和林氏族谱,然后在《湄洲屿志略·世系图》结尾郑重其事地加上按语说明:“(林)愿为神太高祖,非父也,各书记载多误。神父实名林惟慤,兹据祖祠神主并族谱更正之。”可以想见,对于本朝皇帝妈祖封号这样更加庄重的大事,他务必更加谨慎,不会马虎。 蒋维锬先生1990年在《妈祖文献资料》第360码,谈及嘉庆五年妈祖封号,还照录杨浚《湄洲屿志略·封号》所载,曰“垂慈笃祐”云云。其文末“按语”还特别说明:杨浚“在《褒封》中对前人记载作了综合校勘考证,……有参考价值,故予全录。” 为什么要如此关注杨浚(1830-1890年,字雪沧、健公、昭铭,晚号冠悔道人)呢?至少有6条理由。 1、杨浚是清咸丰至光绪年间福建省第一流的硕儒、文史学者。他乃清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毕生肆力于学,才气超迈,博闻广识。凡诗文史籍无不涉猎,且勤于笔墨,留下了等身著述。更先后掌教漳州丹霞、霞文及厦门紫阳、金门浯江各书院,育人无数。杨浚尤精于考据,作风严谨,“惟纪事非隶典则不文”;特别是对闽人、闽神之考据、整理,清代无出其右。 2、杨浚对藏书殚精竭力。其十三岁始购书,一生辛勤搜求,从无倦怠。其于学也着实用心至微。其钱塘好友张景祁称:“杨雪沧先生天才卓砾,博极群书,著述等身,雄视海内,主东南坛坫者垂四十年。鸿笔钜儒、辍学门徒奔走门下,仰之若岱宗斗极。”“又为一切考据之学,凡朝章国故、士习民风无不探摭綦详,舄然成帙,藉以启迪后学”。同治间,他在省城塔巷办正谊书局,主持重刻其家藏的《正谊堂全书》;书成,奏保补用道员。又设“群玉斋”书肆,广搜善本,聚出7万卷,建“冠悔堂”藏之。对于赵文楷遵旨到福州“南台冯巷天后宫”加封天后之诗,诗题又因版本有所争议,杨浚不会不闻不问吧?作为考据家、藏书家、出版家,予以考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吧。 3、同治四年(1865),杨浚援例为内阁中书,充国史、方略两馆校对官。这期间,他饱览清宫档案,查究书刊误讹,应该易如反掌。 4、杨浚精勤于金石研究,对金石孜孜搜求寻觅,成果丰硕。“公通子史百家言,于古今篆籀之学靡不研究,工书法,能作掰窠大字”。他在《六十初度感怀》诗中,述自己一生醉心金石的感受是“摩挲金石起歌声,环堵终朝拥百城”。杨浚与同里陈柴仁、龚显曾等相交甚契,自谓:“每聚首论文,尤喜校雠金石,嗜痂有同癖。”“重重结石交。喜得他山助,频求于野爻。”福州南台天后宫珍藏的镌刻嘉庆妈祖封号的“四字碧瑶”,他极可能就近早已观赏过了。 5、杨浚交游广泛,视野广阔。封疆大吏(做过左宗棠幕僚)、学界名流,文人贤士、省内才俊等,均与之唱和往来,彼此推重。' 6、乾隆五十一年(1786),其祖父自晋江曾坑乡迁居至省城振纪铺经商,迄嘉庆朝时,因贩玉入关之令解禁,遂又往来贸易于姑苏、厦门间。嘉庆十八年(1813),杨浚之父挈家眷落户省城定居,因地处侯官,遂为侯官人。身为福州人,岂能不分外关注家乡福州之事?(以上引述,参见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馆刘繁2013年发表的《杨浚著述辑考》) 1987年妈祖羽化千年纪念日,妈祖裔侄孙、莆田文史界元老林镗先生发表《关于妈祖的家世和她的传说》。文中引述的妈祖嘉庆封号也是“垂慈笃祐”,(引文见《蔓草吟丛——林镗诗文集》第156码,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 1989年春,林祖良(时任莆田市博物馆副馆长、妈祖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编著的《妈祖》画册(福建教育出版社、香港联合出版社出版),登载了福州汀洲州会馆天后宫清代的一副屏风拓片,其中镌刻的“嘉庆五年封号”,也是“垂慈笃祐”(全部正楷大字)。与杨浚《湄洲屿志略》所载封号可互为佐证。据说,该屏风由林鸿年撰书。 林鸿年(1804-1886),字勿村,侯官(今福州)人,清嘉庆九年(1804),道光十六年状元及第,是福建省清朝时期的第一个状元,也是莆田第一位入二十四史的著名人物,莆田著名孝子林攒后裔。道光十八年(1838),林鸿年奉旨为册封琉球国王正使,赐一品服。在琉球160天中,廉洁自守,屏绝馈遗,禁止随从人员携货勒迫销售。琉球国送使者的“宴金”,也却之不受;还将清廷所发出使费节余钱240万贯,悉数交与琉球国王进行赈恤,赢得琉球举国上下的感戴。归国后,著《使琉球录》,记述此行的经过和见闻。回乡后,任正谊书院(现福州第一中学前身)山长,培养出包括陈宝琛、林纾、陈衍、吴曾祺等栋梁之才百余人。工诗,善书法。因此,林鸿年应福州汀洲会馆天后宫撰书妈祖封号、传说之屏风,也在情理之中。 福州汀洲会馆天后宫,与毗邻的南台冯港天后宫是近在咫尺的姊妹宫。据省文物专家考证,南台冯港天后宫很可能就是福州台江下杭街的马祖道天后宫。1800年闰四月十三,赵文楷奉圣上谕,约请福州官员,皆着朝服,出城到南台冯港马祖道天后宫,祭拜妈祖,并将嘉庆御书的“垂慈笃佑”匾额挂在妈祖庙前(顺便提及,嘉庆帝楷书极佳。笔者见过1814年他为莆田明代宫廷画家李在《圯上授书》题跋)。 而汀洲会馆位于上杭街白马南路262号,会馆屋檐下有一对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月“清流沐恩信绅、诰封中宪大夫沈兴应敬立”的古石柱:“海国安澜神庥远播;汀州蒙泽庙祀长崇。”馆内还有三副石柱联:“天也盖高上界,神灵周四海;圣其合应母仪,赫濯表三山。”“千百祀馨香弗替俎豆重光,十八滩风浪胥平舟航普济。”“圣颂播千秋母德参天坤仪配地,慈航周万国湄洲沛泽汀郡蒙庥。”至今保存完好,历历可见。 也就是说,上杭街的汀洲天后宫与下杭街的南台天后宫(马祖道天后宫)彼此邻近,古今都属于同一街区(福州最著名的商贸区双杭街)。如若汀洲天后宫对嘉庆年间所加封号存疑,走过街一查比邻的南台天后宫嘉庆御书的“垂慈笃佑”匾额,或者“四字碧瑶”卵石镌刻便可一清二楚。换言之,汀洲天后宫清代镌刻的“垂慈笃祐”屏风,是铁板钉钉,字字千钧,绝对不会出错的。 1990年元旦,鹭江出版社授权美国某公司全球出版发行的《妈祖圣迹》,其卷首所刊天后妈祖的嘉庆封号,亦为“垂慈笃祐安澜利运”云云。该书扉页和大红缎面封底,都赫然盖有湄洲祖庙的硕大宝印。 直至去年,即2013年10月,台湾著名妈祖学者王见川教授主编之“新港奉天宫文化系列丛书”《近代妈祖经卷文献与郑成功信仰资料》第四卷第68码(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嘉庆五年的妈祖封号,也赫然为“垂慈笃佑”云云。王教授应该是经过充分考证,排除争议之后做出的正确判断吧。 正因为清宫档案所记相左,历来有关人士见仁见智,各持一端。因此,如果我们继续一味拘泥于档案文字,难以正确判断是非。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嘉庆妈祖封号还有相关文物和有关大臣的著述记载可作考证。 文物是不会说谎的。嘉庆五年闰四月初八日,钦差正副使赵文楷、李鼎元同抵闽省。赵文楷旋于十三日恭诣福州南台天后宫宣读加封祭文等。当年,他仿佛就有预感似的,特地将“垂慈笃祐”四字封号,镌刻在了一块玲珑可爱的卵石之上(即《槎上存稿》中的《加封天后“垂慈笃佑”四字,命臣文楷于福州致祭,礼成恭纪》诗中所云的“十行丹篆下,四字碧瑶镌。”) 清代册封琉球共计8次,其中除了康熙年的莆田人林麟焻外,还有3次均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十三年正使齐鲲、道光八年正使林鸿年、同治五年正使赵新。 赵新同治四年(1865)作为清代最后一位正使册封琉球,归国之后撰写《续琉球国志略》(收入其全集《还砚斋全集》,现存光绪八年即1882年福州黄楼木刻版)。《续琉球国志略》中,《道光十八年谕祭天后文(二道)》和《同治五年谕祭天后文(二道)》,4次复述妈祖嘉庆年封号皆为“垂慈笃佑”;而且,光绪年福州黄楼木刻版笔画清晰,历历在目。然而,刘文中,两次引证赵新的《续琉球国志略》,居然都改“佑”为“祜”,以证明自己“正确”! 杨浚在《湄洲屿志略》(清光绪十四年木刻版,福建师大图书馆藏书)之“封号”、“祀典”、“奏疏”等篇章中,5次(分别见诸第39码、75码、76码、124码、130码。无论作者还是刻印工,总不会连错5次吧——何况书中文字笔笔清晰),根本不存在刘文所谓的“‘佑’字,撇画很短,与‘祜’极相似”,“可解释为杨浚误书或手民之误刻”云云(因此,《妈祖文献史料汇编·著录卷·湄洲屿志略》统统私自将“佑”字篡改为“祜”)。 根据礼仪,册使的谕祭文是由礼部和翰林院预先拟定、审核的;何况,钦差大臣是代表皇帝宣读的,金口玉言,绝无出错的道理吧。 再说,嘉庆年间镌刻、珍藏于福州南台天后宫的“垂慈笃佑”四字碧瑶,那时肯定还“健在”无损吧。作为钦差正使的赵新如有疑问,前往查核一下,应该也是易如反掌吧! 赵新(1802-1876年),侯官县人。咸丰二年进士,清重臣、大儒梁章钜的女婿。后授翰林院检讨、历充国史馆总撰、日讲起居注、文渊阁校理、考官等。也就是,他是一位精通国史、文墨者,而且长期接触清宫文档。如果说连他也搞错了不久前的妈祖封号,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弄不好,可能还会掉脑袋。 请读者注意一下1865年这个时间节点——这年,杨浚担任内阁中书,充国史、方略两馆校对官。它与1857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建巡抚庆端联名奏章中所称的“垂慈笃佑”,以及1888年杨浚《湄洲屿志略》5次称“垂慈笃佑”,恰好构成了前后有序的时间链条,彼此呼应。 为慎重计,笔者还查阅了《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九三种·使琉球国志略》。其中所载,同样清清楚楚为“垂慈笃佑”。这部鸿篇巨著,由台湾大学周宪文先生集台湾众多学者专家,穷十五年心力,搜集海内外图书馆珍藏编辑而成。丛刊共309种595册,累计字数4800万字,是台湾有史以来最重要也最庞巨的学术工程。 然而,蒋维锬《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档案卷》第98码,引载的赵新《续琉球国志略》所记妈祖嘉庆封号,却自行“订正”为“垂慈笃祜”,并且不加任何说明。面对编纂者如此主观、粗暴的强行“订正”,真不知《妈祖文献史料汇编》中涉及的50多处“笃祜”,究竟哪些才是史料之真迹?至今,“中华妈祖网”依然沿用此误,并且更名为《祈祭文》《报祭文》,实为以讹传讹。 第三,为了自圆其说,刘文还杜撰出一个所谓封号“没有重复字”的“定例”来,宣称“妈祖64字全部封号中,是没有重复字的,它符合古代封号的定例。”“‘垂慈笃祜’之前妈祖已有‘福佑群生’封号,……这里再用‘祐(佑)’就显得重复了。” 然而,就在他自己随即引述的所谓的“妈祖全部64字正确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敷仁’(天后之神)”,其中,“仁”、“佑”二字,不是已经重复了吗?这不是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吗?借用刘氏自己的话,这不是明显的“随意猜测和妄言”吗? 更加怪异和难以理解的是,刘氏认定的所谓“妈祖全部64字正确封号”中,居然去掉了康熙首封、乾隆再现的“天后”二字——何况“天后”乃妈祖封号系列之中最高、最神圣者也!《湄洲妈祖志·历代褒封》之第213码明白写道:“可以认定是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妃为天后”;214码曰“清乾隆二年加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该书216码总述道:妈祖“神牌全称作: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祜、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祐敷仁天后之神。”该书第217码《历代朝廷褒封一览表》中,再次重申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晋封天后”,“乾隆二年(1737年)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紧接着,第 220码《妈祖历代褒封封号》所载同上,又一次予以确认。经查阅,无论纸质的还是网络的,提及妈祖封号均有“天后”二字。我们不禁要问,刘氏如此捉襟见肘、削足就履地无视“天后”封号,依据何在?如此随意妄为是否大不敬耶? 再说,何以见得封号就不能重复用字?福建另一位几乎与妈祖齐名的女神陈靖姑,历代朝廷20多次褒封之,如唐昭宗封的“护国临水夫人”,宋太宗封的“顺懿夫人”,清咸丰帝封她“顺天圣母”,还有“天仙圣母”、“通天圣母”“太乙仙姑”等等,其中不是也有多个重字吗?重复就是强调嘛——不是有一种修辞格就叫“反复”吗?通过封号反复赞颂妈祖的“仁爱”与“保佑”有何不妥呢? 第四,刘文郑重其事引证的“清丁午《城北天后宫志》书影”中的所谓“垂慈笃祜”,其文字本身就疑云重重,难以为证。 查阅蒋维锬、周金琰辑纂的《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档案卷》第69码《城北天后宫志·加封天后神号祭文》,文章来历不明,疑点诸多。正如蒋维锬先生在文末“题记”中所质疑的:“这是一篇独树一帜的文章,即把褒封昭告与祭文合而为一。此文赵文楷《槎上存稿》和李鼎元《使琉球记》均未收录。不知《城北天后宫》编者丁午是从哪里抄来的?”刘福铸却用蒋先生质疑的奇文来作为自己的论据,真令人匪夷所思。其实,仔细读来,这篇所谓“独树一帜的”、“褒封昭告与祭文合而为一”的文章,并不符祭文的格式体例(看看结尾便知,连“伏维尚飨”之类祭文的应有结语都没有。难怪蒋先生戏称之为“独树一帜的”)。总之,此文乃伪托之作的可能性极大——自身难保,焉能为据?不妨再次借用刘文中的一句:“对于这种只取所需,不及其余的文革式的做法,我们在这里表示强烈鄙视。” 在此,我们有必要严正指出:蒋维锬、刘福铸为了显示自己判断的“正确无误”,公然五次将杨浚《湄洲屿志略》书中清清楚楚的“垂慈笃佑”,篡改为“垂慈笃祜”;4次将赵新《续琉球国志略》书中的“垂慈笃佑”,篡改为“垂慈笃祜”。这种通过篡改史料以证明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否如刘氏所云“凡是对论点不利的材料,作者往往加以隐瞒以蒙蔽不明真相的广大读者”呢? 不仅如此,刘氏还公然撒谎,说什么“关于光绪十四年(1888)杨浚《湄洲屿志略》清刻版原文,与许氏所引颇不一样,正确文字为:‘嘉庆五年,奉旨福建湄洲神庙于封号上加增垂慈笃佑四字。’这里的‘佑’字,撇画很短,与‘祜’极相似,可解释为杨浚误书或手民之误刻。”刘氏所说的文字在该书第75码,请读者看看原文照片,哪有什么“‘佑’字,撇画很短,与‘祜’极相似,可解释为杨浚误书或手民之误刻”云云?试问,对于这种卑劣做法,要不要同样“表示强烈鄙视”呢? 看来,要从学术上彻底辩明“笃祜”“笃祐”之孰是孰非,还得来一番刨根究底。 首先,从文字方面的顾名思义。 “祐yòu”与“祜hù”,虽然读音各异,但偏旁相同,容易混淆。“祐,本作佑。”然而,清档案所载,偏偏写做“祐”而不是更容易区别的“佑”;所以,有些编纂者看走眼了。再则,就文意而言,“垂慈笃祐”与“垂慈笃祜(福)”似乎都说得通,这也是造成张冠李戴的重要原因。作为比较:咸丰五年(1856)写挂惠济祠殿的赐匾即为“安流锡祜”,而同治十三年(1874)写赐江苏华亭等县龙神庙用匾则为“安澜显祐”。可见“祜”“佑”有别,不可混淆。 从词语搭配看,当然也是“锡祜”、“笃祐”、“显祐”,而不是什么“笃祜”。所谓“佑”,《易经·系辞》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祜”,形声字。从示,古声,本义为福、大福。福,也有祜的意思,含有赐福、福佑之意。《诗经·信南山》:“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说明这是寿福。词语“神祜”,意为“神灵所降之福”。经查,清朝有习语曰“常珍笃祜”、“齐眉笃祜”。前者意思是说时常珍惜祖上的美德与福荫;后者意思是说这一家人夫妻和睦,祖上也有美德。 “笃”,则是厚道、真诚、一心一意之意。《尔雅·释诂》:“笃,厚也。”《诗·唐风》:“硕大且笃。”“笃”,还有切实、确凿之意。《论语·先进》:“论笃是与,君子者乎?”相关词语如:笃信、笃情、笃重(专一深重)、笃论(确当的言论)、笃见(确切的见解)…… 据此,“笃祜”的大致意思即厚福、切实赐福的意思;可引申为福佑之意。“笃佑”的意思较为通俗、明白,即真诚、确实、一心一意地庇佑、保佑。 虽然“佑”与“祜”,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字。哪一个可能性更大、合理性更强呢? 就“保佑”而言,“佑”字一步到位,直奔中心,简洁明快,通俗明白;而“祜”——福——赐福、保佑。何苦不“截弯取直”,搞“弯弯绕”呢? 其次,推理毕竟不等于历史真实。我们不妨进一步认真深入思考:究竟是“垂慈笃佑”,抑或“垂慈笃祜”,更符合当时褒封的历史背景?因为从古到今,对于人物的褒封或表彰,都不是随心所欲、任意为之的,其命名定位,必须名副其实,名至实归。也就是说,首先要“正名”,避免“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凭借封号本身的含义与历史事实的比对,顺理成章地来还原真相,推演正名。 其中最主要的,即嘉庆皇帝此次对海神妈祖加封的缘由何在? 根据《清代妈祖档案资料汇编》,嘉庆皇帝的这么3道上谕说得十分明白: 其一,《著玉德派员往厦门虔谢天后助册使平安使琉等事上谕》曰:“该使等远涉重洋,波涛险阻,兼以海盗未靖,正深厪念。今放洋七日即平安驾驶至该国,此皆赖海神垂佑”。 其二,《内阁关于册封使平安回闽,发去藏香交玉德代为祀谢天后上谕的记注》曰:“此皆仰邀天后海神显昭灵应,叩感之余,倍深寅敬。” 其三,《著内阁再拟加增天后神号并撰祭文,令册使赵文楷赍往福建致祭事上谕》曰:“沿海地方崇奉天后,仰承灵佑昭垂,历徵显应。……现在各洋面巡缉兵船及商船往来,均赖神力庇佑。著该衙门再拟加增四字,并著翰林院衙门撰拟祭文,即交此次册封琉球国正使赵文楷赍往福建”。编纂者还有这样的一段“校记”可作注脚:“按清朝传统的加封程序,一般是待册使回朝复命时奏请,经皇帝批给礼部议题,再由内阁撰拟封号呈交皇帝圈定。而这次嘉庆帝破例采取事前主动加封的做法,此中原因,或许就是此件上谕说的“现在洋面未能一律安静”,“各洋面巡缉兵船及商舶往来,均赖神力庇佑”。” 其次,从当事者的出使历程看,更是历尽艰难,所幸有惊无险。 李鼎元《为吁请加封天后父母事奏摺》曰:“此次臣同正使臣赵文楷于嘉庆五年五月初七日乘西南风开洋,于初十日酉时陡遇东北风,暴势甚猛烈,巨浪如山.实为危险。……臣同赵文楷虔祷天后,风即渐息,……迨自琉球回舟于十月二十九日行抵温州外岛北屺,风色不利,舟甚危急,又经虔诚叩祷,遂骤得顺风。自洋面至五虎门计程七百里,一夜便到。……遇险得安,往来迅利,该国人及内地民人皆称神异。及臣抵闽后乃闻六月间飓风击碎艇匪船一百余隻,是皆我皇上至诚感格,故屡致灵应如此。”出使之前,他还特地到京城天后宫祈祷发愿“此行仗神默佑归,定吁请褒封”。 赵文楷在《槎上存稿》中写道:“舟至大洋,从人皆惧,哇吐者相枕藉。……雨翻盆而直注,浪山立而扑人。”回来后,他在《为册封琉球事竣内渡回闽事奏摺》曰:“俾臣等冬月回渡时亦得安稳遄归,荷圣慈之垂厪,益感激以难名。今往返重洋,计期半月,皆仰托皇上鸿福,天后海神显佑”。 第三,从相关官员的奏疏看。 闽浙总督玉德《为遵旨祀谢天后事奏摺》:“该册使等远涉重洋,正殷垂厪。兹处称舟行迅速,开帆六日即已平安抵岸。……臣遵即虔诚斋戒,恭赍香束,亲诣天后宫海神庙敬谨祀谢,并默祷灵昭显佑,将在洋盗匪悉数歼擒以安商旅而荷神庥,仰副圣主绥靖海洋之至意。” 玉德《为册封使船平安回闽事奏摺》:“文楷等船隻于十月二十五日自琉球那霸府开行,一路风帆顺利,……往返重洋,波恬浪静,毫无阻滞。此皆仰赖圣主洪福,是以天后海神灵显默佑。” 直至咸丰七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建巡抚庆端联名跪奏之正式奏章《为请颁匾额事奏折》中,还一再称颂天后“虔祷庇佑遂即陡转南风妥速抵津”、“宣显赞顺神佑弥隆”云云。 总之,以上所述,其主题皆是感恩妈祖保佑平安。其感恩保佑的色彩处处可见,而且“佑”字历历在目,比比皆是:“垂佑”“庇佑”“灵佑”“显佑”“默佑”“绥佑”“神佑”“仰叨神佑”“虔祈昊佑”“虔求佑助”“获邀神佑”“佑彼津途”;反之,“祜”字不曾冒出过一次!因此,从事出有因、“文从字顺”的角度着眼,“垂慈笃佑”也比“垂慈笃祜”来得自然顺畅。 刘福铸文中除了上述4处论证方面的明显硬伤外,还有两处很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刘文一开头就提出:“许更生的《妈祖研覃考辩》”首篇对“《湄洲妈祖志》等书中出现的‘辅国护圣’和‘垂慈笃祜’两个封号大做文章”云云。可惜,刘先生不幸恰恰说反了。我指出的是,古今各种版本的《元史》,以及郎瑛、赵翼、杨浚、柯邵忞等明清文史学家均表明,元顺帝所加的妈祖封号是“辅国护圣”,而并非《湄洲妈祖志》等书认为“谐音之误”的“护国辅圣”。 其二,刘文认为,本人称林镗先生为“莆田文史界元老”,“则是许氏为抬高自己身价所封赏”。其实,查阅词典,元老乃“比喻各行各业中资深望重的人”。那么,林镗先生是否可算行业中“资深望重的人”呢?考虑到林先生逝世多年,许多读者未必知晓,特作如下简介。 林镗(1904-1994),号声甫。北伐时弃笔从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宣传科长。1927年厦大国学系毕业,相继任教于省立莆田高级师范学校、省立福州第一中学等。曾倡办兴化青年艺术社,编辑《福莆仙导报》《莆田县政府公报》《抗战论坛》等多种报刊。1949年9月,任省立莆田中学(莆田一中前身)代理校长。莆仙籍著名作家、教授、学者郭风、俞元桂(福建师大中文系主任)、戴学稷(福建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等,都是其学生。林先生执教50余年,《莆田教育志》为其编撰《林镗本传》。 林镗师还担任过莆田县政协委员、城厢区人大代表、福建省诗词学会首届理事、莆田市诗词学会首届副会长。郭沫若赞其“旧诗有新意,具见功力。”善书法,莆阳寺庙匾额、楹联、志铭多出自他手笔。80年代,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等邀请其为《兴化文献新编》特约撰稿人。晚年受聘于莆田县志办点校《乾隆莆田县志》,还点校过刘克庄、余怀、林兆恩、江春霖的作品。1984年评为“全国健康老人”。 2003年6月,莆田市政协主席林文豪为其诗文集《蔓草吟丛》题词曰:“揄扬先德,风雅常新;保存文献,嘉惠后人。”戴学稷先生《序》言中写道:“对我说来,林镗先生是乡贤、前辈和老师。抗战胜利前,在我进入省立莆田中学念高中时,他已经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知名教师,……对他是很景仰的。”“回顾数十年前往事,缅怀先生之高风亮节,道德文章,仅略就所知,书此以表对先生的敬仰。”国家一级美术师、当代著名书法家、福建诗词学会顾问、福建楹联学会会长赵玉林先生序言曰:“林镗先生献身教育事业,为国育英,功不可没。热爱诗词,在继承并发扬传统、振兴诗坛上作出了贡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有功于文化事业的人。……如此磊落胸襟,无愧人师!……为书景仰之情如上。”(以上引文均见《蔓草吟丛——林镗诗文集》,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 我想,不必过多引述了吧。时至今日,我对于自己称呼林镗先生为“莆田文史界元老”毫不后悔。我真不知道,如此尊称耆德硕老、多才多艺的一代名师有何不妥?更不明白,自己作为晚辈后学如此称呼先贤,怎么会是“封赏”,又何以能够“抬高自己身价”呢? 注:刘福铸《是“垂慈笃祜”,不是“垂慈笃祐”——许更生<妈祖研覃考辩>商榷》全文刊发于《海洋视野下的妈祖文化与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港文学选刊》2014年增刊),《湄洲日报》摘要登载于2014年11月6日)。 |